发布日期:2026-01-09 10:00点击次数:56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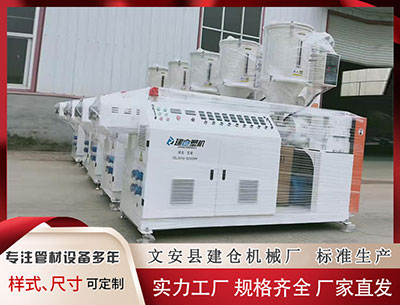
秦始皇统一六国克拉玛依塑料管材设备厂家,奠定帝制根基,却被后世频繁追问:为何偏偏留下赵高这个祸根?
这个问题本身,就建立在一个错误前提上——秦始皇从未将赵高认作祸害。
赵高在秦始皇生前,非但不是隐患,反而是被倚重的近臣。
要理解这其中的逻辑,须抛开后见之明,回到秦帝国建立之初的政治结构、人事制度与身份认知之中。
赵高的存在,不是秦始皇的疏漏,而是秦制内在逻辑的自然产物。
赵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太监”。
这不是语义辨析的游戏,而是关乎历史事实的澄清。
他并非幼年净身入宫,而是在成年之后因罪受宫刑,才成为“宦者”。
这一细节,决定了他在宫廷中的角定位与社会身份的演变轨迹。
若将他简单归类为“阉宦”,就等于用后世对宦官的刻板印象,覆盖了秦代宫廷职官体系的真实面貌。
赵高的身世,在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中有明确记载:“赵高者,诸赵僇疏属也。
赵高昆弟数人,皆生隐宫,其母被刑僇,世世卑贱。
”这段话看似简短,却信息密集。
后世对“诸赵疏属”的解读,长期存在分歧。
主流观点认为赵高出身赵国王族远支,但这种理解忽略了秦代“诸某”结构的特定用法。
在《史记》中,“诸田疏属”指齐国田氏宗室,“诸赵疏属”同理,应指秦国宗室中姓赵的一支。
秦国王室本为嬴姓,但因先祖曾被封于赵地,故亦称“赵氏”。
秦始皇名“嬴政”,亦可称“赵政”。
因此,“诸赵”即指秦国宗室成员。
赵高虽属远房,血缘疏远,但确为宗室子弟。
这一身份,是他得以进入权力核心圈层的原始资本。
“皆生隐宫”一句,常被误读为赵高兄弟天生残疾或自幼入宫。
这是对“隐宫”一词的严重曲解。
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《云梦秦简》明确指出,“隐宫”是秦代刑徒劳作的场所,属于国家手工业体系的一部分,类似于后世的官营工坊。
赵高之母因犯罪被罚入“隐宫”服刑,在此期间生下赵高兄弟。
2009年公布的《张家山汉简·户律》进一步佐证,“隐宫”在汉初仍沿用秦制,指代刑徒聚居劳作之地。
因此,赵高并非生于深宫,而是生于刑徒劳改营。
他的出身卑微,但宗室血统并未因此被抹除。
这种“血统高贵、处境卑贱”的矛盾状态,构成了他早期人生的基本张力。
赵高踏入仕途,靠的不是血缘恩荫,而是业技能。
他在自述中称:“高固内官之厮役也,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,管事二十余年。
”所谓“刀笔之文”,即指文书处理能力。
秦代官僚体系虽以军功爵制为骨干,但行政运转仍依赖大量文吏。
赵高出身“刀笔吏”家庭,父亲或祖父即为此类职官,他通过世袭或荐举进入宫廷文书系统。
这不是靠关系,而是制度安排。
秦制并未完全打破世职传统,尤其在宫廷内部事务管理上,技术岗位往往父子相承。
赵高凭借对律法条文的娴熟掌握与高执行能力,逐步获得秦始皇注意。
须强调,秦代“宦者”与后世“宦官”概念截然不同。
Q Q:183445502“宦”泛指君主身边的侍从人员,包括文吏、车夫、侍卫等,并不特指阉人。
赵高初以“刀笔吏”身份入宫,后升任“中车府令”,负责皇帝车马仪仗,属于近侍要职。
这一职位虽无军政大权,却因日日随侍君侧,具备高信息通达与信任度。
清代“仪銮使”可作类比,和珅正是以此职起家。
赵高能担任此职,说明秦始皇对其能力与忠诚有充分认可。
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记载:“秦王闻高彊力,通於狱法,举以为中车府令。
高既私事公子胡亥,喻之决狱。
”此处“私事”并非暗中勾结,而是指赵高以私人身份辅导胡亥学习法律。
秦始皇安排赵高教导幼子,恰恰证明对其信任。
建筑业里总共七千万人,其中将近六千万是农民工,企业减岗裁员先裁的就是他们,因为要先减少农民工施工队的业务,可这些农民工不算城镇就业人口,就算下岗失业也不计入失业率,看起来建筑业没什么压力,苦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。
近年来,受宏观调控政策、金融环境变化、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速度的影响,房价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。一线城市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房价依然坚挺,但调控力度不断加强,部分区域出现调整迹象。二线、三线城市则在政策引导下,房价涨幅趋缓甚至出现回调。
但暂时不会买房的人特别纠结,因为他们自己也害怕房价突然一下又迎来大幅上涨,甚至出现大幅翻倍。
一、先搞懂:公积金的“隐藏价值”,比利息重要得多
别慌,国家早就说了:住宅用地到期自动续期,房子还归你家!不过,房产证写谁名字可有讲究,家提醒:
胡亥为始皇少子,教育安排经深思熟虑。
赵高精通“狱法”,即司法审判程序与律令适用,这在秦代是高阶的业技能。
他能被委以此任,说明其法律素养在当时属顶尖水平。
然而,赵高后来“有大罪”,蒙毅依法判其死刑,并削除宦籍。
具体罪名,司马迁未载。
后世猜测纷纭,或涉贪腐,或涉僭越,皆属无据推演。
史料只明确两点:罪行足以判死;秦始皇终赦免。
赦免理由为“高之敦于事也”——即赵高办事勤勉,态度认真。
这里没有“求情”“包庇”等现代政治想象,只有君主对有用之才的惜才之举。
秦始皇并非无视法律,而是行使君主高裁量权。
秦制虽重法,但君主始终凌驾于法之上,这是法家思想的内在悖论。
值得注意的是,蒙毅并未因赦免赵高而失宠。
《史记·蒙毅列传》称其“位至上卿,出则参乘,入则御前”,地位远高于赵高。
蒙毅是秦始皇真正的心腹,可同车共乘,出入禁中。
若秦始皇真有意保全赵高而牺牲蒙毅,史料有蛛丝马迹。
事实是,蒙毅依法判罪,秦始皇依法外施恩,两者并行不悖。
这说明在秦始皇眼中克拉玛依塑料管材设备厂家,赵高只是办事得力的工具型人才,蒙毅才是政治伙伴。
赦免赵高,不是偏袒,而是权衡利弊后的实用主义选择。
赵高受宫刑,是其人生转折点。
宫刑不仅是身体摧残,更是社会身份的彻底剥夺。
在秦代,宫刑意味着从“人”降格为“刑余之人”,虽可留任,但永仕途上升通道。
赵高原本凭借宗室血统与业能力,尚有晋升可能;宫刑之后,政治前途彻底断。
这种身份落差巨大。
但须强调,史料未载其受刑后的心理变化,不可臆测“怨恨”“报复”等情绪。
只能说,宫刑使其从“可能的臣子”变为“纯粹的奴仆”。
秦始皇三十七年驾崩于沙丘,赵高已侍奉二十余年。
推算其入宫时间,应在始皇即位后十年左右。
这意味着赵高完整经历了秦统一战争、郡县推行、律法整饬等重大事件。
他不是局外人,而是体制内资深参与者。
他对秦制的理解,远一般官僚。
这解释了为何他能在始皇死后迅速策划政变——他熟悉制度漏洞,掌握信息渠道,知道如何利用胡亥的无知与李斯的犹豫。
后人常问:秦始皇为何不除赵高?
答案很简单:赵高从未表现出威胁。
在始皇生前,赵高守法、勤勉、业,是理想的技术官僚。
他的“祸害”属,只在权力真空时才显现。
帝国继承机制的脆弱,才是根本问题。
秦始皇未立太子,未明定继承程序,导致死后权力迅速失序。
赵高只是抓住了这个空隙。
若始皇早立扶苏,或明确辅政班子,赵高纵有野心也难成事。
赵高能成功,还因秦制本身存在结构缺陷。
军功爵制虽打破贵族垄断,但宫廷内部仍保留大量世袭、封闭职位。
赵高以宗室远支身份进入系统,本就说明血缘仍是准入门槛之一。
同时,秦法严密却缺乏弹,官员唯法是从,缺乏政治判断力。
李斯身为丞相,竟被赵高以“安危在君”一语说服,放弃原则,正反映秦官僚体系过度依赖程序、缺乏价值判断的弊端。
赵高的“祸”,不在其人,而在其时。
他是秦帝国制度逻辑的产物,也是其崩解的催化剂。
始皇信任他,不是昏聩,而是制度使然。
在那个时代,一个精通律法、办事可靠、出身宗室的近臣,本就该被重用。
谁能预料,这样一个“敦于事”的人,塑料管材生产线会在君主死后掀翻整个帝国?
赵高后来的作为,如逼死扶苏、蒙恬,杀李斯,弑胡亥,皆载于《史记》。
但这些行为发生在始皇死后,不能反推始皇识人不明。
历史不是侦探小说,不能以结果倒推动机。
始皇时代,赵高无任何不轨记录。
将帝国灭亡归咎于留用赵高,是后世史家为简化因果而设的道德寓言。
真正值得深思的,是秦帝国权力结构的端集中。
始皇揽大权,不设辅政,不立储君,使帝国如精密钟表,一旦发条停摆,立即散架。
赵高只是一个伸手拨动齿轮的人。
若无赵高,有李高、王高。
问题不在个体,而在系统无冗余、无制衡。
赵高的身世之谜,长期被“阉人”标签遮蔽。
事实上,他先是文吏,其次是宗室,后才是刑余之人。
这三重身份叠加,使其在秦制中处于特位置:既有技术能力,又有血缘法,又因刑罚而彻底依附皇权。
这种依附,在和平时期是忠诚的保障;在动荡时期,则成为破坏的杠杆。
《史记》未为赵高立传,只散见于他人列传,说明司马迁也未将其视为立历史主体。
赵高是工具,是变量,是制度裂隙中的机会主义者。
他的“祸害”形象,是汉代史家为凸显秦亡教训而强化的。
在秦人眼中,他或许只是个能干的中车府令。
2009年《张家山汉简》公布后,学界对“隐宫”的理解趋于一致。
这纠正了千年误读,也了赵高真实的出身环境。
他不是深宫阴谋家,而是刑徒之子,在底层挣扎中凭借才学突围。
这种经历,使他既懂律法,又谙人情,更知权力之可贵与脆弱。
秦始皇赦免赵高,不是感情用事。
在秦制逻辑下,一个精通狱法、办事勤勉的官吏,其价值远大于一次罪行的代价。
死刑可抵,人才难求。
始皇的选择,符法家“以功覆过”的实用原则。
后人以道德视角批判,实为时代错位。
赵高与胡亥的关系,常被描绘为“狼狈为奸”。
但史料仅载赵高“喻之决狱”,即教授法律。
胡亥年幼,学习律令是皇子教育常规内容。
赵高作为中车府令兼法律家,承担此责情理。
两人日后勾结,是权力突变下的临时联盟,非长期预谋。
蒙毅判赵高死刑,体现秦法之严;始皇赦之,体现君权之尊。
两者并存,恰是秦制本质:法为君用,非君为法用。
赵高案不是法与情的冲突,而是君主意志与官僚程序的协调。
蒙毅依法办事,始皇依法外施恩,各司其职,无矛盾可言。
赵高受宫刑后,仍任原职。
这说明秦代对刑余之人的使用,并不局限于洒扫杂役。
只要能力足够,仍可掌实权职位。
这与后世宦官权的背景不同。
赵高的权力基础是业能力,非宫廷身份。
秦始皇死时,赵高已掌管玉玺、符节、车驾等关键信物。
这不是偶然,而是制度安排。
中车府令本就负责皇帝出行仪仗与印信保管。
赵高能控制信息、伪造诏书,正因其职位赋予的法权限。
问题不在用人,而在制度未设防伪机制。
帝国崩溃的速度,暴露了秦制的脆弱。
从始皇死到胡亥立,仅数月;从胡亥立到天下大乱,不过两年。
赵高能在如此短时间内操控全局,说明权力结构本就失衡。
一个近侍能左右国运,非其能,乃其位。
赵高后来指鹿为马,测试群臣忠诚,常被视作疯狂之举。
但放在秦制语境下,这是理的权力确认行为。
秦法严苛,官员唯上是从,缺乏立判断。
赵高需要确认谁真正服从自己,谁仍忠于旧秩序。
指鹿为马,是端环境下的忠诚筛查。
赵高终被子婴所杀。
子婴以“称王”而非“称帝”继位,暗示秦帝国已名存实亡。
赵高的死,不是正义战胜邪恶,而是权力更迭的然。
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功能:加速旧秩序的崩解。
回看赵高一生,他从未主动挑战秦制,反而始终在制度框架内行动。
教胡亥法律,是职责;受宫刑后留任,是制度允许;伪造诏书,是利用职位权限。
他的“恶”,是制度缺陷的放大,非个人道德败坏。
将秦亡归因于赵高,如同责怪齿轮转动太快,却无视机器设计错误。
《史记》对赵高的记载,始终冷静克制。
司马迁未用“奸佞”“祸国”等词,只客观陈述其行为。
后世演绎,层层加码,才形成今日“赵高=宦官=祸根”的刻板印象。
剥离后世滤镜,赵高只是一个在特定制度下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技术官僚。
秦始皇留用赵高,不是疏忽,而是然。
在一个依赖律法、强调率、血缘与能力并重的体制中,赵高这样的复型人才,本就该被重用。
他的存在,不是漏洞,而是秦制成功的证明;他的反噬,才是秦制失败的警钟。
赵高的案例,揭示了技术官僚在高度集权体制中的双面。
他们能高执行命令,却无法承担价值判断;他们忠诚于程序,却可能背叛目标。
秦始皇需要赵高这样的人推行政策,却未防范其在权力真空时的破坏力。
历史没有如果。
但可以确定的是,即便没有赵高,秦帝国仍可能因继承危机、制度僵化、民力透支而崩溃。
赵高只是加速剂,非病因。
将复杂历史简化为个人善恶,是对历史的粗暴对待。
赵高生于隐宫,长于律法,成于勤勉,毁于宫刑,终于乱世。
他的一生,是秦帝国兴衰的微缩景观。
看懂赵高,才能看懂秦制;看懂秦制,才能理解为何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,会在短短十五年内灰飞烟灭。
赵高的“祸害”标签,是后世史家为道德教化而贴的。
在真实历史中,他只是一个被时代选中、又被时代吞噬的普通人。
他的悲剧,不在作恶,而在被赋予了越其角的历史重量。
史料未载赵高早年志向,未载其受刑时的感受,未载其与胡亥密谋的细节。
这些空白,不应由想象填补。
我们只知道:他精通法律,办事勤勉,受过宫刑,掌过玉玺,改过诏书,杀过大臣,后死于非命。
这些事实,已足够勾勒其历史坐标。
秦始皇看不到身后事,正如赵高看不到自己会成为亡国象征。
历史人物的评价,常由结果决定,而非动机。
但研究历史,须剥离结果,回到过程。
在始皇眼中,赵高是能臣;在汉儒眼中,赵高是奸臣。
两种视角,皆有其理,皆有其蔽。
赵高不是例外,而是典型。
他的崛起与陨落,映射出秦代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与内在矛盾。
理解这一点,比追问“为何留祸根”更有价值。
赵高的故事,不该被简化为忠奸对立,而应被视为制度与人的复杂互动。
在一个以法为纲、以君为天的帝国里,一个精通法条、贴近君侧的人,自然拥有巨大影响力。
这种影响力,在秩序稳固时是助力,在秩序崩解时是杀器。
秦帝国的覆灭,不是一个人的错,而是一套制度的限。
赵高站在这个限点上,被推成了替罪羊。
但真正的问题,始终在于那个设计了这套制度、却又拒为其设置安全阀的人——秦始皇本人。
赵高留下的,不是祸害,而是一面镜子。
照见秦制的辉煌,也照见其脆弱;照见始皇的雄才,也照见其盲点。
这面镜子克拉玛依塑料管材设备厂家,至今仍值得凝视。